□郑国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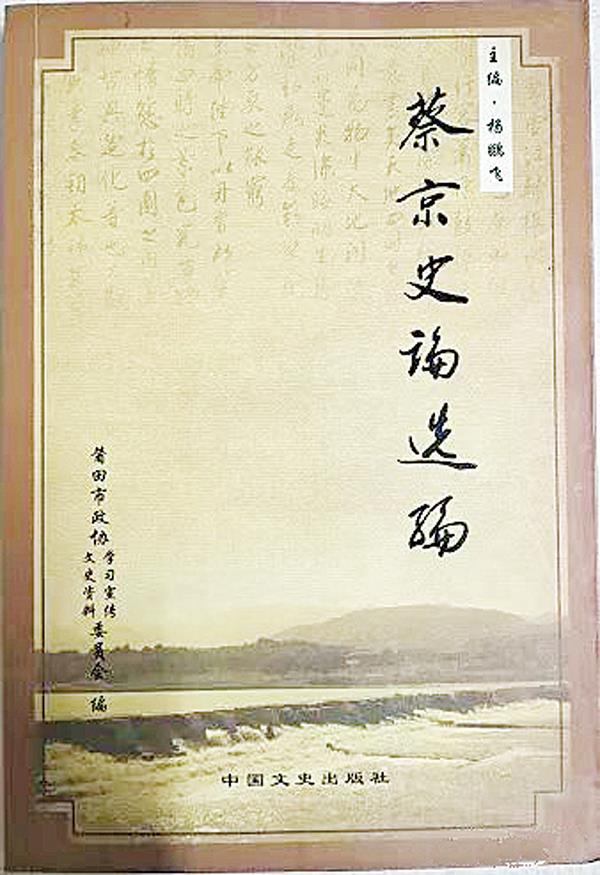
我其实并未看过枫亭“游灯”。印象较深的倒是宋诗宋词中“上元灯节”的描绘;少时看《水浒》连环图,看到浪子燕青在上元之夜潜入东京李师师的家中,关心的是燕青通过李师师打通宋徽宗的关节如何招安,关心的是梁山英雄好汉们的命运,连李师师家中如何灯红酒绿都不在意,更不会关心街上热闹的花灯了。有一年在远离枫亭几十里的莆仙交界处一个小村看到游灯,入夜时分,村民们扛着灯架游弋于木兰溪两岸,没有锣鼓,也不放鞭炮,宁静的夜色中昏黄的灯龙在缓缓移动,有一种遥远的古老的气息微微传来……
猛然记起多年前已有一篇《难忘家乡龙灯游》,出自我一位朋友的笔下:
“每年元宵节,我的家乡利角村及毗邻的海头、东海、大埔、东沙四个村,都要举行一场热闹非凡的游灯盛会。每个村至少要出一条灯龙,灯龙由灯头、灯身和灯尾组成。灯头由各种造型别致的大灯笼点缀而成。灯身由一节一节的灯架集合而成,每节灯架上有八至十盏不等的点着蜡烛的灯笼。一节灯架由一户人家举着。灯尾呢,有的是抬菩萨,有的是敲锣打鼓。每当元宵节夜幕降临时,一条条的灯龙穿梭于各个村庄之间,那披红戴绿的男男女女,那飞光流彩的灯海,那热热闹闹的鞭炮声,那五彩缤纷的烟花,令人如醉如狂。”
朋友姓蔡,却与他的几万蔡姓乡亲一样,大都忌讳为蔡京的后裔,而拜宋代清官蔡襄为祖。为此,蔡氏族人曾与莆仙文史界的老人们多次闹得不可开交。
文人当面不敢坚持,过后都会不无讥讽地提起秦桧的后人秦涧泉,以及他在西湖岳飞墓前的那对名联:“人从宋后羞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。”
莆仙人忌讳蔡京,以至于有关蔡氏一门在长期当权时引进东京戏曲艺术回故乡的资料,散失在史海的茫茫烟波之中;只有枫亭杨亚其老人保存一本一直秘不示人的《连江里志·上卷》抄本(枫亭旧名连江里)。我们这次找到枫亭旧街见到他,老人经过一番犹豫,终于从楼上拿出这个抄本,该书第二条就是:“《山房遗稿》卷五载:宣和末,蔡攸(蔡京长子)以灯事色乐游枫亭,置画舫于江上,使教坊女弟妆扮故事以侑酒。”(江是枫江,流入湄洲湾,不是木兰溪。)
这则简单的文字传达了两条重要历史信息:一是枫亭及其邻近地区独特的元宵游灯习俗源于宋代;二是蔡京父子(特别是蔡攸)是戏剧由北方引入莆仙地区(包括闽南)的关键——“使教坊女弟妆扮故事”。
莆仙戏的源头充满着太多的传说,而真实的来历却资料奇缺,这不能不归因于蔡京。
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,对神圣或神奇的东西一贯持怀疑态度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看到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,内载宋方天若《木兰水利记》,编者明代郑思亨跋其云:“……莆人遂讳京功,并讳天若记。予不以人废言,姑特存之。”
“莆人遂讳京功”之说吊起了我对蔡京的好奇。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阅了《宋史》《莆田县志》《仙游县志》和《仙溪志》,得出结论:所有这些传说都缘于“讳功”,这种脆弱幼稚的地域文化心理,类似于当代的“血统论”。而历史的真实是:蔡京执政二十三年,任命了不少亲信(含莆仙籍官员)担任福建地方官,这些地方官秉承他的旨意,建造了大量的水利桥梁等公共设施,因而,在北方连年战乱的大背景下,福建“民安土乐业,川源浸灌,田畴膏沃,无凶年之忧”(《宋史·地理志》),海上交通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。南路入粤东,北路抵永嘉,西北至赣、浙,泉州港成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。
限于篇幅和能力,我无法梳理北宋新旧两党交争的是是非非,也无能力为蔡京的是非功过一一作出评判,只提一下蔡京当权时“狠抓落实”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。“贫有养、病有医、死有葬。”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,安济坊以医民之贫病者,漏泽园以葬贫亡者与客死荒野者。
这样的好政策未必得到认真的贯彻,还可能受到顽强的抵抗,如果受到“名人”的反对,那后果就更糟了。著名诗人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:“崇宁……置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,所费尤大,朝廷课以为殿最,往往竭州郡之力,仅能枝梧。”老百姓还要编歌谣骂娘:“不养健儿,却养乞儿;不管活人,只管死尸。”
长期的官场斗争锻就了蔡京的铁腕性格,“盖军粮乏、民力穷,皆不问。若安济等有不及,则被罪也。”因而州县领导“宁左勿右”,纷纷“奉行过当”。最后倒霉的不是别人,而是蔡京。国家灭亡了,没有人敢去骂那位“风流天子”,而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在蔡京头上。当时的风气是:“今日江湖从学者,人人讳道是门生。”
蔡京一生喜爱莆仙音乐和戏剧。激烈的政争之余,童年熟悉的旋律,是抚慰心灵消解乡愁的灵丹妙药。《拾墨记》说:“蔡京每有宴会乐工辄奏乡音。”《连江里志·事类》也说:“蔡太师作寿日,优人献技,有客以丝系童子四肢,为肉头傀儡戏。”
世上无人不好高。权力可以使人得意忘形,更何况是权倾朝野,一人当轴之时,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载:“左楼相对,郓王以次彩棚幕次;右楼相对,蔡太师以次执政里幕次……诸幕次中,家妓竞奏新声,与山棚露台上下,乐声鼎沸。”
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危险性,嫁接在第二代身上,往往更加可怕。蔡攸把乃父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攸“得预宫中秘戏,或侍曲宴,则短衫窄裤,涂抹青红,杂倡优侏儒,多道市井淫蝶谑浪语,以蛊帝心。”(《宋史》卷四七二)“宣和间,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,自为优戏。上作参军趋出,攸戏上曰:‘陛下好个神宗皇帝!’上以杖鞭之曰:‘你也好个司马丞相。’”(周密《齐东野语》)
甚至还有出格得离谱的言行。《宋史》记载:徽宗封了个副宣抚使让蔡攸跟童贯去讨伐燕山,年轻的蔡攸高兴得不得了,认为此行获胜唾手可得。临行前到宫里向徽宗告辞,见徽宗身边的嫔妃实在漂亮,竟不提打仗的事,而指着那两个嫔妃说:“我打赢了这场战争回来,您把她们赏给我。”徽宗听了并没有不高兴,反而笑了。
物极必反,盛极必衰。金兵攻陷汴京,徽宗退位南逃,钦宗执政,亡国的罪责谁来负?皇帝是不能有错的。于是,蔡京作为“六人帮”之首被流放,行至潭州(长沙)而死。死前曾作《西江月》,词云:八十一年住世,四千里外无家。如今流落向天涯,梦到瑶池阙下。玉殿五回命相,彤庭几度宣麻。只因贪恋此荣华,便有如今事也。
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短短八句,足可谓之一部中国版的《忏悔录》。
蔡京死后,执政者说蔡攸之罪不减乃父。乃下诏贬至万安军(广东万宁),后派人把他杀了。还连累他的弟弟,钦宗在杀他的诏书下加了三个字“亦然”。
事隔四十一年南宋高宗下诏,把拘管了多年的蔡京家人“放令逐便”。有意思的是,同时解放的还有忠臣岳飞的老婆孩子。重获自由的蔡京家人遵照他的遗愿,将其遗骸运回家乡枫亭,安葬在赤湖(今九社村地界)。
几年前的正月十五,在午间朋友聚餐时,我们就《三希堂法帖》中的蔡京的书法谈起他的为人种种。饭后,直奔枫亭。一路打听,终于来到枫亭镇九社村的一片枇杷林中。蔡京坟前的石马石羊已被他的乡亲偷光卖光,唯有仙游县政府立的石碑没人要,却也被推倒在地。当地九社村是“山地开发先进村”,坟地的龙眼树下,又加栽了密密麻麻的枇杷树。
离开蔡京坟,我们从蔡氏故里赤岭东宅村穿过,跨过一道小桥,越过九涧,来到了梅岭脚下。在村里一位老者的引导下,找到了蔡氏祖坟。老坟的坟头比普通的坟头大了一倍多,被高及人头的荆棘和杂草包围着,是多少年无人疏理的结果。只有坟头之上,有人新近压上一叠纸钱,在山间的微风中轻轻颤动。老者告诉我们:“蔡家祖坟大风水是座笔架山,左右山脉有五瓣,犹如五条苍龙直插赤湖深渊,有‘五龙盘珠’之美名,所以蔡家出了左右两丞相。”——这就是无人疏理祖坟,却有人为其压纸钱的解释。
最近我再次来到枫亭,在蔡京墓地,枇杷树已不见,龙眼树下曾被推倒的石碑已重新竖立。石碑前,是一丛丛刚刚烧烬的香灰,那袅袅轻烟仿佛还未散尽…… (备注:本文于2011年被收录到《蔡京史论选编》。有删节)

